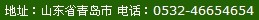|
(编者按:今天是端午节。胶东方言当中,端午一般读作“当午”。在胶东农村过“当午”,有很多讲究。下面就听栖霞隋建国先生一一道来。)以下是正文——小时候最盼望过节,如过年、清明、端午、七夕、中秋等,往往待快到了板着指头算,因又要吃上好东西了。然而记忆深刻的还是端午节。端午节对胶东栖霞人来说是一年中重要的节日。如今尽管以往传统的民俗节日淡薄了,但每到端午节这一天拔艾蒿,折桃枝大多栖霞人都仍在沿用。家住城区的居民也驱车外出采集艾蒿等药材放在门顶上,祛病消灾已经成为习俗。说起来话长,从50年代初我记事起,端午节就在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我的记忆中,那时候胶东栖霞,过端午重点是小孩子要轧撸束、跟着母亲拉露水采草药,其重点是拔艾蒿。记得那时候每到端午节那天我们还在睡梦中,母亲就在我们兄弟俩的手腕和脚腕上轧(ga方言,即缠绕)上了“撸束”(方言,即五彩线)。有时候我醒了,总闭着眼假装不知道,精心享受着母亲的爱。那幸福,那温暖,那欣慰,那甜蜜,至今难以忘怀。那时候,每年的端午节前,大街小巷不时的有挑担的货郎手摇拨浪鼓,吆喝着叫卖。货担子上有各种颜色的线车,叫“撸束线”。每到一处,周围都围满了大人孩子。根据需要,按尺或线的根数多少割着买。我家里没有钱,母亲就用织布剩下的碎线头染成各种颜色,捻在一起给我们当“撸束线”。尽管颜色不如买的鲜艳,但我们挺喜欢,也觉得挺美。因这是母亲的心血。记得端午节那几年,每当天快亮了,母亲把我们叫醒。我一睁眼,除了我们手和脚上有“撸束”外,窗棂子、门槛、门吊环上等都缠上了五彩线,美极了。我伸出胳膊,抬一抬脚,感到无比自豪,因自己比以往俊了,美了。我们刚下了炕,母亲就拿着篓子领着我们出门“拉露水”。在路边长满青草和艾蒿的地方,母亲用手沾点露水檫脸,并让我们也学着用露水洗脸。说用端午的露水洗脸可以消灾祛病。我们一边踏着露水走,一边拔艾蒿和挖“道切切”“马蒿”“接骨草”“布布丁(蒲公英)”“西瓜香”“甜茄”“鬼枕头”“银钱谷”“山面汤”“板苍腿”“马荠菜”“麦子”“山麦子”等多多山药材。这些都要在太阳出来前完成,这才叫拉露水,是端午节的重头戏,否则不灵。艾蒿回家放在街门顶上和窗台上辟邪消灾,其它药材存放在背阴处,备防病治病专用。吃粽子是端午节的必备食品。那时候家里买不起粽子叶,母亲就事前领着我们到村西边的沙沟河边拨一些芦苇叶子当粽子叶。粽子三个角放上长果仁(花生),外部用稻草(稻子秸秆)缠绕,煮熟了那味道可香了。有一年我妈妈上山劳动没有时间包粽子,就在锅里摊上芦苇叶子,上面放上大米让我们放学回家自己烧火蒸。嗨,那味道也挺美,和粽子味道差不多。端午节后的第一场雨,母亲就让我们用剪子剪去手和脚上的“撸束”扔到院子里,说是让它变成“曲线”(方言,即蚯蚓)随水流到海里让鱼吃。待我们长大了才知晓那是纪念屈原。就是“撸束”在雨水中转化为蚯蚓到江河中喂鱼,以此保护爱国诗人屈原的躯体。刚开始那阵子,我们带着“撸束”最不喜欢下雨天,妈妈都是强逼着我们割掉扔到雨水的院中,因我们还没有喜欢够。无奈在母亲的好说歹说下,只好不情愿的割痛去爱了。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随着当今生活的改观,以往的民间传统节日习俗逐渐淡薄了。但那幼时美好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。假若时间若能倒流,我多么想再回到当年,偎依在母亲的怀里,再一次享受一下母亲在手腕和脚腕上轧“撸束”的亲情啊!(“撸束”应为禄寿的转音)预览时标签不可点
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xixiazx.com/xxsdl/4699.html |
当前位置: 栖霞市 >胶东乡村记忆栖霞农村过端午节,都有什么讲
时间:2020/7/23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栖霞广电讲堂传统媒体的转型融合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